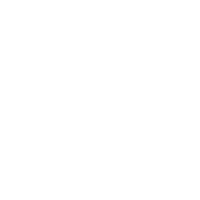足球新闻
-
费兰:我们坚持到最后逆转取胜,要享受这个冠军&并渴望赢得更多

-
阿斯:巴萨球员列队迎接皇马球员领奖,仅贝林厄姆未握手祝贺

-
今夜见证红军加冕23:30利物浦主场战热刺 不败即锁定英超冠军

-
中超第9轮比赛集锦 长春亚泰1比2不敌成都蓉城

-
郑浩乾:确实等了很长时间才再次取得进球 帮球队获胜是最关键的

-
9轮3分!海牛1-1梅州客家仍垫底 恩戈姆破门韦林顿-席尔瓦点射

-
生涯首进任意球!姆巴佩任意球直接破门,弹地球打进死角

-
曼联在英超客场完成25次射门,为球队自2020年以来最多

-
西足协主席:希望球迷享受决赛 我们与裁判委员会、俱乐部合作

-
高天意对阵山东泰山打进3球,这是他对单一对手进球并列最多的

-
入乡随俗!30岁纳萨里奥庆祝结婚12周年纪念日,给妻子买足金耳饰

-
西媒:瓜迪奥拉与妻子在尽力挽回婚姻,他承诺每周回巴塞罗那一次

-
每体:巴萨计划让特狮当主力门将3C担任替补,佩尼亚今夏自由离队

-
恢复神速!罗马诺:阿玛德将在下周回归曼联合练

-
【赛后发布会】方大钟:球员们踢得十分努力 回去总结备战下一场

足球录像
- 04月27日 法甲第31轮 斯特拉斯堡vs圣埃蒂安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足总杯半决赛 水晶宫vs阿斯顿维拉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德甲第31轮 法兰克福vsRB莱比锡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亚冠精英联赛1/4决赛 吉达国民vs武里南联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法甲第31轮 勒阿弗尔vs摩纳哥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法甲第31轮 里昂vs雷恩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亚冠精英联赛1/4决赛 横滨水手vs利雅得胜利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冠区域分组赛第1轮 海南双玉vs湖北超级先生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冠区域分组赛第1轮 广西布山vs五华华京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国王杯决赛 巴塞罗那vs皇家马德里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乙预赛阶段第6轮 泰安天贶vs兰州陇原竞技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冠区域分组赛第1轮 南京龙胜vs武汉两江金岸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乙预赛阶段第6轮 长春喜都vs山东泰山B队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甲第6轮 定南赣联vs广西平果 全场录像
- 04月27日 中乙预赛阶段第6轮 无锡吴钩vs江西庐山 全场录像
足球集锦
- 法甲-莫雷拉埃梅加均传射建功 斯特拉斯堡3-1圣埃蒂安
- 足总杯-水晶宫3-0完胜维拉队史第3次晋级决赛 将战曼城森林胜者
- 德甲-克瑙夫双响埃基蒂克传射 法兰克福4-0大胜十人莱比锡
- 亚冠-马赫雷斯闪击菲尔米诺破门 吉达国民3-0武里南联将战新月
- 法甲-比雷斯破门扳平 摩纳哥1-1勒阿弗尔
- 法甲-拉卡泽特破门托利索建功 里昂4-1胜雷恩
- 晋级四强!利雅得胜利4-1横滨水手 C罗生涯934球杜兰双响马内破门
- 中冠-海南双玉0-11湖北超级先生 孙玉鹏卢正杰帽子戏法
- 中冠-广西布山1-2五华华京 赖健涛点射致胜
- 三杀!巴萨加时3-2皇马夺第32座国王杯 孔德116分钟远射绝杀
- 中冠-南京龙胜0-3武汉两江金岸 罗智翔梅开二度
- 中甲-定南赣联连扳两球2-2广西平果4轮不败 唐诗任意球破门
- 距欧冠区6分!米兰2-0威尼斯先赛仍第9 S-希门尼斯普利西奇建功
- 6轮不败!苏州东吴2-0上海嘉定汇龙 科维奇连场破门梁伟棚建功
- 中甲-广东广州豹2-0佛山南狮 若昂-卡洛斯传射建功商隐破门